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jindaishi/detail_2012_05/19/14659097_4.shtml
七七事变后国军嫡系伤员吃米面 杂牌军粗粮不管饱
2012年05月19日 12:49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王世江方军
核心提示:同 样是军人,待遇却如此不平等,嫡系部队的病号每天吃大米白面,供应我们“杂牌军”伤员的却连粗粮也不管饱;嫡系部队病号要什么药有什么药,我们这些从前线 回来的每天只能用消毒水和盐水洗伤口。最令人难忘的是这年的“双十节”,蒋介石的第三重伤医院“慰问”伤病员时,给嫡系部队的病号每人发十元钱,给“杂牌 军”的伤员每人发五元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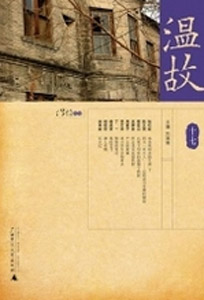
2005年10月,我去辽宁锦州采访了抗战老兵王世江。九十一岁的王世江是卢沟桥事变的亲历者,是我迄今采访的唯一的从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士兵,又到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任职到军分区司令员一级的军人。
王世江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牡丹江军分区的司令员。我和老人一见面,第一件事情,就是看那枚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由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颁发 给他的纪念章。能够领到抗战胜利六十年纪念章是一种光荣。我采访过亲历“卢沟桥事变”的大部分幸存者,王世江的政治状态和经济状况应该是最好的。他住在辽 宁省军区第二干休所,房子是二层的小楼,阳光明媚,有一百多平方米。王世江的儿子也是1949年前参加革命的,因此,连王世江的儿子都光荣“离休”了。王 世江单独居住,有个下岗工人帮助他料理家务。听说下岗工人的儿子上了大学,王世江就自觉负担了那个非亲非故孩子的全部学费、生活费。王世江对我说:“我留 着钱没有用。帮助了别人,我最愉快。”
王世江这位九十一岁的老人由于疾病,数年前被截去一条腿。他只能坐在床上接受采访。王世江的思维很有条理性,他不紧不慢地从1936年他参加二十九 军讲起。重点的地方他讲得很细致,我提问的时候他还把问题区分开慢慢回答。快到吃饭时间了,他早安排在他家服务的女工包好了饺子。连着几天采访,我们之间 混熟了,他一会儿操纵录像机,给我们看中央电视台对他的采访录像;一会儿,又坐的床上给我们大家拉一段二胡。这位亲历过卢沟桥事变的老军人始终热情洋溢、 精神矍铄地和我们谈话。
王世江的床头码放整齐的全部是京剧的录音磁带,如果我们没去造访的话,他除去看电视新闻就是听京戏的录音了。
我是一直在做着对亲历抗日战争最后一批人的采访记录工作,残酷的现实常常这样摆在我的面前:“往往是我前脚采访,后脚,被采访者就离去了。”毕 竟,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距离今天七十五年了;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距离今天六十九年了。1945年日本投降、抗战胜利距离今天也已经六十一 年了。
我们都想活埋了这个嚣张的鬼子兵
1933年,西北军在喜峰口英勇抗战,用大刀片杀敌的消息,威震全国。也点燃了我们青年人心中的抗日火焰,都想参加这样的队伍,抗日救国,誓死不当亡国奴。1936年春天,西北军冯玉祥旧部宋哲元回老家山东乐陵招考学兵。我就是乐陵人,喜欢听宋哲元将军的讲话。我在家读过两年私塾和三年小学,我听了宋哲元的话后,就同本县一百多名青年报名应招了。从此,就在国民党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旅当了兵,实现了我参军的夙愿。
那时,我二十一岁,家里人还都劝阻我哩!当时,新兵胸前佩带着白布条,写着新兵二字,还盖着红色的章,看起来特别显眼。那时,司务长领着我们新兵一 百二十人从山东到天津,准备再转乘火车到北平。一路上风风光光,谁知在天津火车站的站台上,突然游荡过来一个日本鬼子,大概是警察。他一看中国人又招兵买 马了,就过来阻拦,不让大家上车。
“在我们中国人的地盘上征我们自己的兵你们都管?!太横行霸道了!”
我当时血气方刚,跑过去和鬼子理论。日本鬼子说:“八嘎呀路!”抬手就给我一个大嘴巴。我也不含糊,一个扫膛腿把日本鬼子撂倒在站台上。恼羞成怒的 日本鬼子随手就掏枪,正巧,跑来两名中国铁路警察,一个警察眼疾手快,一把抓住日本人的手枪,另一个人把我拉开了。一百多兄弟们都义愤填膺,捋胳膊、挽袖 子,非要把这个鬼子就地给埋了,可是,司务长说,咱们先赶路,对于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咱以后再说。
参加了抗日的二十九军,我感到有了用武之地,练好武艺打日本的劲头更足了。不到半年时间,就把西北军的“三大套”(劈刀、打拳、上单杠)学会了,考核成绩优秀,不久被提升为班长。
中国旧军队的愚兵政策
西北军虽然抗战闻名全国,但是毕竟是旧军队,愚兵政策和打骂制度相当严重。新兵入伍第一堂课,讲的是纪律。连长就这样讲:“军队嘛,要绝对服从,比 如,我手里拿一个鸡蛋,它本来是白色椭圆形的,官长偏说它是黑色方形的,你们也要随着说它是黑色方形的。这就叫做绝对服从。”当时听他这样讲,心里很不服 气。但没人敢争辩,怕的是得不到实事求是的回答,反而招来皮肉之苦。长官随便打骂士兵,就连班长也随便打骂士兵。在新兵训练时,没有一个士兵幸免于打骂圈 子以外,轻的“照半身相”(跪在地上),重的“吃锅贴”(用手打脖梗子)和“按两头打中间”(四个人按着四肢,用扁担或竹片打屁股),官兵关系比较紧张。
1937年6月底,二十九军为了宣传抗战,举办大中院校夏令营,高中二年以上的学生参加集训,由一一○旅长何基沣负责,抽调一批干部和班长去任教,我被调去当班长。
西北军是一支抗日爱国的军队,但却因不属中央嫡系而得不到蒋介石的支持,二十九军的军饷时常被无端克扣,逼得宋哲元自己印发钞票,维持所属部队的生存。
你们怎么不提日本鬼子的人头来见我!
1937年7月7日,日寇向北平西南郊卢沟桥中国驻军蓄意挑衅,制造事端。
事变第二天早上,何基沣旅长派我和手枪连一名班长刘树森到二一九团三营督战,侦探日寇的情况。当时我们二人手持德国“自来得”手枪,身着便衣。我们 二人原来只使用过中国生产的“汉阳造”大枪,没有使用过外国生产的手枪,于是,我们悄悄找了一口井,一人照井里开了两枪。德国枪就是好使!我们两个人顺着 高粱地摸索着来到卢沟桥附近,远远就听见有车辆行驶的动静,“呜呜、呜呜”响,只见四辆日本军车开过来。
“咱们在高粱地边上,等过来,咱打司机。”我建议战友。
等车到了离自己二三十米的时候,我们两人钻出高粱地飞跑到汽车跟 前,向最前面开车的鬼子连开两枪,击毙了头车司机,然后转身就跑。
我们宁愿当战死鬼!我们不当亡国奴
负责卢沟桥防区的是第二一九团第三营,日本人开始攻打卢沟桥,旅长何基沣又派我们去探视守桥情况,三营金振中营长当场向我们表态:“放心,日本人决不能从我这边过去,我们一步也不能退”。
不一会儿的工夫,日军开始了第一次冲锋,敌人的战车来了,装甲车后边跟着步兵,战士们都红眼了,着急要开火,金营长说:“不打,听我命令,不到有效距离不打。”
我随战友们趴在地上,等车开到距离防区三四十米远的时候,营长一声令下“开打”,顿时间,乒乒乓乓的枪声、战车声交织在一起。
金营长还跳出战壕向战士们挥臂喊话:“兄弟们!我们宁愿当战死鬼!我们不当亡国奴!——杀鬼子的时候到啦——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敌立功啊!”
我心里很是痛快啊,可是还手了!
“换大刀片,上!”军令如山倒,战士们抬手甩掉帽子,挥刀直奔敌人,
当时的日本鬼子最怕大刀片了,他们刺枪过来,只要我们一闪躲过,回手一刀,敌人的手腕就被砍掉了。”敌人当时是死的死伤的伤,只好撤退了。
当时二十九军还没有装备那么多的电话,金营长命令我们二人先撤出战斗,跑步去见旅长何基沣汇报初期战况。旅长何基沣听了高兴地用拳直砸桌子:“打得好!你们再去三营,转告我的话,给我多杀鬼子!立功受奖!”
赶到二一九团时,正遇日寇向三营阵地再次冲击。日军几次突击我军的阵地,他们把汽车围上钢板当“装甲车”,边打机枪边冲锋,步兵跟在“装甲车”后一 窝蜂似的往上涌。营长金振中立即下令用穿甲弹射击敌“装甲车”,一阵阵排枪向敌人“装甲车”打去,子弹飞离枪口的声音和命中敌“装甲车”的声音几乎连在一 起,乒乒当当地在三营阵地上响成一片,把敌“装甲车”穿了许多窟窿,打得敌“装甲车”掉头就跑。跟在车后的敌步兵抱头鼠窜,狼狈不堪。
[何基灃為中共秘密黨員潛伏於國軍,後在國共內戰的徐蚌會戰中令國軍2萬士兵倒戈投共
怪不得整篇文咁煽情,d情節都好流下]
“司号员,吹冲锋号!”金营长适时向部队下达了全线出击的命令。
一阵冲锋,又打死打伤敌人好几十个,并击毙了日军指挥官松游少将,日军连许多尸首都没顾得上拖走,就灰溜溜地逃窜了。
7月9日,惨败的日军又以飞机大炮猛攻宛平城,我二一九团指挥员浴血奋战,不仅保住了宛平城,而且夺回了已被日军占去的龙王庙等地。
砍汉奸的脑袋示众
日军代表恼羞成怒,拔刀直逼何基沣。何基沣在二十九军是以“粗暴”闻名的,他毫无惧色,拔枪迎了上去,倒是鬼子悻悻地先放下了军刀。这样打打谈谈,在卢沟桥附近双方进行了十几天拉锯战。十几天之后,日军大批增援部队开到卢沟桥,战场形势起了大变化。
这时,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急需接济给养、弹药和增援。我们早听说蒋介石派 了嫡系孙连仲的二十六路军开到河北增援。卢沟桥的守军日夜盼望援军快到,可是一等不到,二等不来,孙连仲到了河北的涿县,距离北平只有几十公里就按兵不动 了。就在我们二十九军打得十分惨烈的关键时刻,孙连仲的二十六路军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不但不增援二十九军,反而掉头南逃,一直退到黄河南岸,说是奉了蒋介 石的命令,要据守黄河天险。于是,
“卢沟桥事变”,我们二十九军牺牲数千将士。宋哲元在日军优势兵力的压迫下,不得不撤出北平。
1937年9月29日,我随何基沣转战撤退到河北省泊镇附近。这时一一○旅改编为一七九师,何基沣任师长,我在该师手枪连当班长。这天午饭后敌机又来轰炸,我们当场抓住两个给敌机指示目标的汉奸。
“怪不得这几天敌机跟着我们轰炸,原来是这两个汉奸天天指示目标给敌机!”
“这两个家伙该剐!”战士们摩拳擦掌,议论纷纷。
何基沣大步走过来命令道:“王世江!你把这两个汉奸带到泊镇车站砍头示众!”
这时,已经离泊镇不远了,我带上几个弟兄把这两个汉奸押到车站处决后,便急忙赶回师部。听见师部附近枪声不断,有情况了!只见几百个日军武装便衣从 我侧翼潜入,突然包围了我们师部。手枪连连长张跃蒲率领全连迎击敌人,掩护师长何基沣。与敌激战两个多小时,连长张跃蒲和排长李连壁阵亡,全连伤亡过半, 我也受了重伤,一梭子机枪子弹扫过来,其中一发打断了我的左大臂,臂上的肌肉被打掉一大快。
那天是1937年的中秋节。
那天,连队还包包子吃呢……敌人的歪把子机枪扫过来,我带的一个班十个人,六人牺牲,二人受伤。我中弹后由于失血过多多,整个人都已经虚脱。东倒西歪的,站不住……
……当时两个战士架着我撤退,我们身边的高粱被子弹打得唰唰地成片折断。
……当时真是“混天地黑”,跑着跑着由于高粱地里尽是泥水,所以,鞋掉了一只。
“鞋!我的鞋掉啦!”我喊。
两个架着我的战士说:“班长!别要鞋啦!要命吧!”
在“七七事变”中对蒋介石的印象
突出重围后,我们汇合了部队向南撤退。
我和杨世亨在济南站下了铁甲车。济南本是个美丽的城市,这时也简直成了人间地狱。到处是河北逃难来的难民,他们无依无靠行乞度日。伤兵杂在难民中根 本无人过问。而国民党军政要员只顾自己逃命要紧,还有谁来管我们几个叫花子似的伤兵!我们托了人情,苦苦哀求,才能在济南市协和医院挂上号。一个医生一打 开我臂上的裹脚带,臭气四溢,伤口里的烂肉脓血中已经生蛆,蛆虫四处乱爬。医生掩着鼻子皱着眉,十分武断地说:“必须把胳臂锯掉!”
抗日战士怎么能没有胳臂?不得已,含恨离开济南。
“七七事变”不久,济南也被日寇占领了。
“七七事变”的枪伤终于好转
我们随逃难的人流逃离济南之后,打听到山东的兖州有个国民党第三重伤医院。杨世亨架着我上了火车到了兖州,住进国民党第三重伤医院。在医院里,看到 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病号住在整齐、干净的房间里,我们这些从抗战前线卢沟桥下来的重伤员却拥挤在铺着麦草的地铺上,心里很是不平。一个抗战军人为国家流血牺 牲本是份内之事,只要能治好伤,睡草铺也行。但是,同样是军人,待遇却如此不平等,嫡系部队的病号每天吃大米白面,供应我们“杂牌军”伤员的却连粗粮也不 管饱;嫡系部队病号要什么药有什么药,我们这些从前线回来的每天只能用消毒水和盐水洗伤口。最令人难忘的是这年的“双十节”,蒋介石的第三重伤医院“慰 问”伤病员时,给嫡系部队的病号每人发十元钱,给“杂牌军”的伤员每人发五元钱。我入院两天后才来个医生查房,这个医生看了我的伤口,用手捂着鼻子说: “你的伤口已恶化,另外伤口太大也无法愈合,看来你这个左臂非锯掉不可。”
“我还要重返前线抗战,怎么能把我的臂锯掉呢?”
“你的想法很好,可是舍不得一只臂,恐怕连性命难保。”
我生气地说:“保不住性命我也决不锯臂!”
他最后说:“那你再想一想吧。”
这个医生不但没治疗我的伤,反而给我增加了思想负担,使我几天几夜没睡好觉,伤口恶化也越来越严重,蛆蚜满身爬。露出的骨头都变黑了。正在我苦恼的 时候,一位有爱国心的年轻军医十分同情我,来给我换药,治疗。一次他给我换药时说:“你咬咬牙忍着疼,我用小刀把你骨头上的灰尘刮掉,慢慢就会愈合。”听 他一讲,我又喜又怕。心想,关公一边刮骨疗毒,一边下棋,谈笑风生,难道一个抗日战士死都不怕,还怕刮骨?我随手把手帕放在嘴里咬住说:“只要能治好伤, 你就动刀吧,大胆地刮吧!”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刮骨,真是钻心地疼。他一边一刀一刀地给我刮骨疗毒,一边不时地看着我的脸色,并用药布擦掉我头上的汗珠, 说:“多忍一会吧,刮干净些会好得快些。”
就这样一刀一刀,把我的伤口里的脓血烂肉和骨头外层变黑的骨头都彻底地刮了一遍。刮后不到十天,果真看到有新生的肉牙,后来慢慢长出了新肉,伤口一天天逐步愈合起来。
“七七事变”之后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悲伤结局
由于“杂牌军”在医院受到排斥,激怒了伤员,东北军和西北军的伤员联合起来,砸了医院,打了院长之后,凡能行动的伤兵大部分都离开了医院。我因为参加了这次活动,虽然伤未痊愈,也实在难继续住院治疗,便随之自动出院归队。
就在我受伤的时候,蒋介石命令孙连仲部的二十六路军把守着黄河渡口,不让宋哲元部南撤,宋哲元被迫沿黄河西溯,退至山西。到山西后,又倍受阎锡山的 排挤。
当时二十九军官兵眼见大好河山一块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只能仰天长叹,无可奈何。我出院回到部队,眼见部队减员严重,蒋介石又不给补充,
当时我们二十九军在“七七事变”之后已经改编成七十七军了,邱晓亭是中国共产党七十七军地下党工委书记,身份是军官。他对我们说:“你们要到延安, 这是正义的举动。像你们这样的爱国青年,全国到处都是,已经到延安的何止千万,如能明确到延安是为了抗日,那么,只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组织起来在旧军队 工作,起的作用会更大。因为你们对在目前的部队人事都熟悉,去延安学习后不一定回原部队工作,岂不是舍近求远吗?另外,延安那个地方并不大,去的人过多, 确实容纳不下,希望你们慎重考虑。”就这样,我于1938年11月1日,秘密参加了共产党。邱晓亭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我们师长何基沣在“卢沟桥事变”之后连连受挫,自戕未遂,被送到武汉疗伤。经过周恩来的介绍,他于1938年1月5日到延安住了一个月。何基沣从延 安回到部队后,思想又和共产党靠近了一步,他曾经多次拿了武器和金钱帮助共产党。1939年1月,何基沣被中共中央批准为正式党员,和我在一个支部,都是 秘密的党员。
[睇下,之後抗日戰爭完全略過中共,因為中共根本無出力打過抗日戰爭]
抗战胜利接收日军缴械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举国欢腾。在七十七军担任军长的何基沣直接命令我去执行缴械日军武器,接受日军投降的任务,我当时是他属下骑兵营少校营长。
当时是10月,艳阳高照。我领了一个班的士兵,前往距离驻防地不远的湖北省武胜关,去接受一个大队的侵华日军的投降交枪仪式。
我们属于第六战区孙蔚如受降官指挥。我们湖北方面有侵华日军第6方面军第一三二师,独立混成旅第八十三、第八十五旅、独立步兵第五、第十一旅集中汉 口。但是,独立第十二旅、独混第八十六、第八十八旅集中武昌,日军投降代表为冈部直三郎,他在汉口向孙蔚如受降官投降。我们缴日本人的枪不是都到汉口去集 中,而是在所有侵华日军中队以上的驻在地进行。日军的驻扎地如果是小队,也就是“连”单位的部队时,他自己就会到相当于“团、营”的日军建制部队去集中。
一起打了八年!谁都知道谁!湖北的日军甚至知道我们七十七军原来就是亲历“卢沟桥事变”的二十九军。而二十九军,原来是中国的西北军。中国西北军本来不是蒋介石政府军的嫡系部队,属于杂牌军。但是,是一支抗击日军的坚强军队。八年来,我们常常俘虏日本兵,他们也常常说起这些故事来。
当时的武胜关是铁路枢纽的一个车站,有相当于一个团的侵华日军把守。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中国的老百姓已经在报纸上知道侵华日军在中国各地交枪投降的消息,他们跟着我们一行人马蜂拥而至。
只见武胜关车站日本军营外面是人山人海、人头攒动、人声鼎沸。
我和一个班的士兵是骑马前去的。到了车站门口,远远望去,侵华日军已经在车站前广场上列队等候。而且,侵华日军军官已经在门口恭敬等候多时了。我和一名士兵走到列队整齐的侵华日军队伍前。
只见日本军官一声大吼,日本军人全体立正,向日本军旗行注目礼。在呜咽、低沉的日军军号下,红条四射的侵华日军旗在车站建筑上徐徐降下。
只见侵华日军军官一声大吼,把挎在身上的指挥刀取了下来,双手捧着,鞠躬弯腰递给我。我接过刀,转身又递给随身的士兵。
万籁俱寂,鸦雀无声,似乎无人相信骄横跋扈的侵华日军会缴枪投降。
我们一共十二个人,十二匹马,缴了六百侵华日军鬼子兵的枪!
日本兵非常有纪律,他们整齐划一,把“三八”步枪和“歪把子”机枪都整齐地码放好,再整齐划一地列队站好。
尽管中国的老百姓欢呼雀跃,他们都涌进日本兵的军营看热闹,放下武器的日军虽然沮丧万分,但是,阵脚不乱。他们列队坐在地上,每人还都戴着军帽,扎着武装带。中国民众也没有对放下武器的日军有不当的行为。
日军投降军官是中佐军衔,这个中佐会中文,他下命令把枪捆扎好,都抬到在铁轨上的汽车上 去。那个在铁轨上跑的汽车烧七成成色的木炭,所以,一行驶就冒大量的烟尘。过去,我们七十七军就是远远地看着这烟尘后,开始计划袭击日军的交通线。今天, 日军中佐和十二名日军士兵,我和一名士兵,押送六百条日军的步枪,十五挺日军机枪,三十门小炮和五十门掷弹筒,大约四十把军刀,四十把手枪和大量弹药—— 起程!向十公里以外,我们七十七军的驻地行驶去……在我军驻地,日军把全部武器卸下,然后,和我们七十七军官兵挥手告别。
[呀屌原來成篇野又係中共既宣傳稿,真係信一成都唔掂]